共治天下
人们想必不愿意承认:自己不懂什么叫共和;但恰恰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什么是共和。我现在就给出一个非正式的定义:
共和者,统治者与其支持者依法共治天下也。
我并不指望有多少人会毫无保留地接受此定义。但我毫不怀疑,“共治天下”肯定是共和不可缺少的要素,或许是核心的要素。需要讨论的是:哪些人参与共治。这件事展开地说来,却不简单,它几乎涉及全部政治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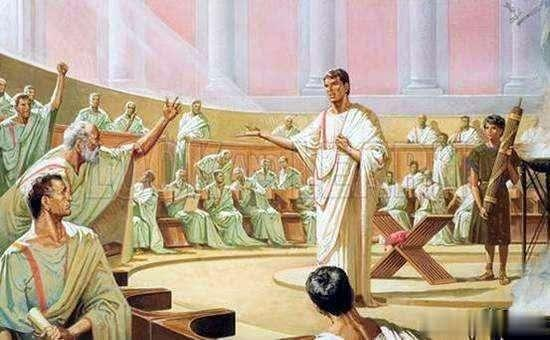
贵族共治
从先秦时代起讲“共治天下”,一点也不荒唐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那时就有共和,更不意味着出现于西周的“共和”是真共和。重要的是,先秦时代确实已经具有某些共和元素。简言之:
先秦时代诸王与贵族共治天下。
这种共治,不妨简称之为“贵族共治”,这等于是省略了作为主体的“诸王”。所谓诸王,当然首先指周王,也包括其他诸侯王,他们可视为头等贵族。在广义上,贵族包括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,后者算是末等贵族。作为共治的参与者,此处贵族指大夫、士,以与占支配地位的头等贵族相对照。
贵族参与下的这种共治天下,可不是做做样子,而是一种很地道的“共治”,而且出自当时的礼法。如所周知,先秦就是一个盛行礼法的时代;孔子及其门徒的著作言论,尽显了礼法的尊严与价值。礼法的作用在于:它严格规范了共治各方的权利与义务。贵族们严格地自觉遵守这些涉及“权利义务”的约束;他们在履行义务时的忠诚、严谨与牺牲精神,谱写了古代史的动人篇章,可以说光照千古!也因此,先秦的贵族共治,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亮丽的一页,让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幸沐浴在古代文明的余晖中!
此后,再没有这样瑰丽的时代了。秦之后的两千年,或许仍然是“郁郁乎文哉”。但你到哪里去找出入宫廷的孔孟墨荀?到哪里去找晋文公与介子推、齐桓公与管仲、楚庄王与孙叔敖、吴王与伍子胥?浸透在孔夫子著作中的怀古之浩叹,无非是悲叹先秦时代早期那种共治秩序的衰微;后世经常说的“古风不再”,多半指贵族共治时代的风范不存了。
先秦古朴原始,而现代共和新颖先进——笼统言之,当然无法反对。但即使对于现代共和,先秦的贵族共治仍不失为一个辉煌镜鉴!
士族共治
初看之下,自秦以来的两千年,就是不折不扣的专制时代,其间岂有共治的影子在?其实不然。秦之后的各朝,都存在某种共治,只是其共治的结构与形式各异罢了。
大体上,汉代、汉之后的魏晋六朝、以及隋唐年代,就是一个皇帝与文臣共治的局面;更狭窄一点说,就是皇帝与丞相共治天下。一连串闪闪发光的名字:萧何、王莽、曹操、诸葛亮、司马懿……,彰显了那个时代丞相的权力之大、声威之隆、功德之盛。
汉代之初,大臣主要来自与刘邦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兄弟。他们多少带有下层阶级的色调。汉代社会的急剧分化,促成了一批世袭权势家族的崛起,这就是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所谓士族。士族具有先秦贵族的某些特征,可视为某种准贵族。在魏晋六朝直至隋唐时代早期,朝廷的文臣乃至丞相,主要就来自士族。因此简而言之可以说:
魏晋六朝与早期隋唐时代的政治,就是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。
从士族身上,可以看到一些贵族的影子,但也仅仅是影子而已。从贵族那里,士族继承的缺点更多、优点较少。这就注定了:士族共治所能提供的正面的东西不多。因此毫不奇怪,魏晋六朝时代,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。士族政治的最大弊端在于,士族在某种程度上的世袭制,是一种完全过时的东西,它维系了顽固落后的权力垄断,严重地阻碍着政治的逐渐开放。
有了如此严重的缺陷之后,从“共治”的角度着眼,“士族共治”就没有多少值得考虑的价值了。
士人共治
唐朝无疑使中古时代的繁荣达到鼎盛。但从政治史的角度看,唐朝的建树也不多,更不是制度建设上的巅峰。这个巅峰来得稍晚一些,它出现在大唐之后的宋朝。在读史者看来颇为诡异的是,宋朝恰恰被认为是一个十分衰弱的朝代,只是它还是赢得了后世的赞颂。
在中国政治史上,宋朝最大的贡献是:它实现了相当发达的士人共治。
皇帝与士人共治天下这种局面,并非宋朝所开创,它发端于隋唐时代。实现与士人共治的前提是科举制,它正是隋唐时代开创并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。
所谓士人,就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。这是一个极为庞杂的巨大群体。作为个人,士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出身与利益取向,并不属于某个单一的阶层。作为群体,士人从未形成为一种充分组织化的政治势力。将士人联结在一起的,仅仅是他们的同一进身之路——即科举之路。基于师生、同科、同门、同乡等复杂关系,士人之间存在某种相互联结的网络,正是这种联结网络让士人们获得某种稳定的归属感。在这种意义上,也可以说,士人组成一个有形的群体,这是古代社会不可多见的一种社会群体。到宋代时,士人群体已经高度定型了。正是这一群体,托起了宋朝的士人共治。
当然,通过科举进入官场——更别说进入朝廷——的士人仅仅是少数优胜者。但这些人或强或弱地联系着所有其他士人。更重要的是,每个不放弃举业的士人,都是官场中的潜在候补者。因此,至少在士人的心理上,皇帝与整个士人群体共治天下,而不是仅仅与官员共治天下。这一点非常重要,它保证了王朝统治基础的宽广。宋代基本上没有内部动乱,既无叛官,亦无叛将,在很大程度上,正是基于士人群体的高度整合、士人对于朝廷的群体性忠诚、朝廷对于士人的高度尊重与高度信任、皇室与士人之间精诚合作关系的高度和谐。这种局面实属史上少见。至于外患不断,那是另有原因在。这就不妨说:
士人共治使中国中古政治达到那个时代的最大成功。
仅此,就不能不说,在政治史上宋代有绝大的贡献。
无产阶级共治
创建于1949年的共和国,有一个今天不那么悦耳的雅名:无产阶级专政。字面上这意味着:无产阶级参与共治而且居于独占地位。有正常思维的人,不太可能认可这一解释:无产阶级就这样当权了?他们难道不如以往一样在工厂、田间干活吗?
这确实是一个令理论家们烦心的难题。在理解上的主要困难就在于:无产阶级中的个人,确实很难有“在掌权”的感觉,就是最强化的催眠术,也不可能催生出这种感觉来,除非是那些完全因偶然机会进入权力的幸运儿,如王洪文、陈永贵等少数人。
只要做一点小改动,上述难题就解决了:将“无产阶级共治”修改为:
领袖与党共治天下。
大概没有人能否定“领袖与党共治天下”;只有一个完全非常态的例外:在文革时期,领袖一度踢开了他自己的党,仅仅与“中央文革”那几个人共治天下了。
如果认可上述结论,同时注意到党的坚实基础正是无产阶级——在“前三十年”这大体上是事实,今天就很难说了——那么,不就达到了“无产阶级共治天下”这一结论吗?
以上论证拐了好几个弯,必定使你觉得别扭,且放过不论。
真正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时代的共治水平,远远低于古代,特别是宋代。首先,无产阶级的成员进入权力的机会很少,且主要还不在其少,更主要的是完全没有稳定可靠的常规渠道,没有一种堪与科举制比美的制度,甚至根本没有建立某种遴选制度的意愿!这样一来,所谓“共治”就成了一句空话,与古代的“士人参政”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其次,就是对于进入了权力的那些人来说,其运用权力的独立性与自主性,也远远低于宋朝那些“志在治国平天下”的士人。
因此,这一时期的“共治天下”是最不成功的。
家丁共治
如上谈及的共治天下,参与对象来自贵族、士族、士人、无产阶级,都是或大或小的群体。一般来说,群体愈大,统治就愈有活力,也愈有合法性。其中尤以士人共治达到最高的共治水平,因为原则上每个士人都有进入权力的平等机会。这一点十分可贵,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政治文明史的最大贡献,其价值远远超过所谓四大发明!
人类的政治进步,无非就是愈来愈多的人参与权力。自远古至今天,政治进步的图景明白而无可怀疑。但局部与一时的倒退亦不少见。倒退的主要表现在:共治参与者在减少。例如,与贵族共治相比,秦始皇就明显倒退了:他仅仅依靠权力金字塔上的极少数官员。正因为如此,秦王朝才亡得那样迅速、那样彻底。
就是秦始皇,也没有退到极端。更坏的政治形式就是家丁共治,这意味着:
独裁者与其少数家丁(即心腹,形同家奴)共治天下。
与“贵族共治”、“士人共治”等等不同,“家丁共治”并不是一种常态,它也不整整占有一个时代,通常是一种短暂或者局部的现象。不过,家丁共治也并非难得一见,历代都有,特别黑暗的年代出现得还不少。在元明两代,就不断出现家丁共治,这两个王朝就几乎亡在家丁共治所造成的空前破坏中。元朝的“家臣治国”,无疑沿袭了草原部落的传统,其落后荒唐不待多说。明朝出了一个最大的家丁,他就是天启皇帝的宠臣魏忠贤。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宦官,被荒淫至极的天启帝赋予全权,位置升到史无前例的“九千岁”。明王朝就几乎亡在天启与魏忠贤这一对现实宝贝手中。
颇为有趣的是,在现代亦有“家丁共治”。那个辉煌一时的重庆王,就是特别借重家丁、最后毁于家丁的统治者。至于文革这种非常态时期的家丁共治,就更不必说了,那时,一个侍寝的生活秘书也是有希望进入权力核心的!
家丁共治当然毫无正面价值,不值得再费笔墨。
精英共治
所有上述的共治与共和的主要差别是:
A. 共治者的“进身之路”,要么是世袭,要么是举荐,要么是由科举选拔,这些都谈不上真正公平,也难以获得真才。在现代共和制下,这些途径都将代之以自由公正的选举。
B. 共治者的进退、奖惩、任免、任期等等,都未纳入严格的法治轨道,或者完全不受约束,致使国家机器得不到正常的净化与更新。而在共和制下,政府的组成与运行完全服从法律的管束。
C. 最主要的差别是最高权力者的地位。就本文所述的共治而言,最高权力者是君主或者领袖,其权力源于继承或者攫取,他构成共治体的单独一方,而且是唯一有自主性的一方,由他认可、征聘或邀请另一方的官员进行共治,而不是经过协商的双方联合共治,共治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称的,最高权力者几乎得不到监督且不可能被罢免。在现代共和制下,最高权力者的权力源于选举,而且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;他与共治者有平等的法律身份。
尽管如此,还是不能说:共治与共和毫无共同之处。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提及的,共治具有共和的某些元素;这种元素愈多,它就愈接近于共和。反过来说,也不妨认为:
共和就是一种高度完善的、而且制度化的共治。
共和制下的共治者,正是古代共治者——贵族、士族、士人——的现代继承者,他们经由法定途径——选举或者其他制度化的遴选途径——进入政界,撑起共和制的整个大厦。他们获取权力的道路是竞争性的,因而必定在能力与德行上具有某种优势,这意味着他们属于一个称为精英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权力精英——的群体。
现代共和制,原不过是由权力精英实行共治的一种制度。
简言之,不妨说共和制就是精英共治。当然,“精英共治”这个词并没有完全表达共和制的内涵。采用这个词,不过是有助于激发对共治与共和的联想而已。
写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