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缘里分
屈原与伏尔泰各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,相隔万里,但两人的故里都被人们纪念着,甚至是争抢着——两湖人争抢屈原故里只差没打架了!只是,没有人知道,屈原与伏尔泰本人,是否特别偏爱或者景仰自己的乡里,是否都认为,自己的乡里恰恰应当是举世无双的人杰地灵之地。真的,乡里的缘分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神圣性吗?看重故乡的缘分真的举世皆然吗?或许,大多数人对此会给予肯定的回答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要独持异议:某块土地成为你的降生之地,是所有偶然事件中最偶然的事件。你的乡缘谈不上有什么神圣意义,更不能说你的故土一定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地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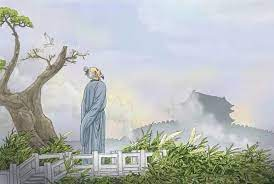
乡情绵绵
需要解释什么是乡情吗?乡情无非是你嬉戏于儿时伙伴中的那种天真欢乐;是你在身赴远乡之时对家乡一草一木的无限眷恋;是你与故土久别重逢时的那一汪热泪……。当你身处异乡,默然低吟着李白的诗篇《床前明月光》时,乡情的力量如何,你会比任何时候都体会得更真切、更实在。
在诗人、作家、游记撰写者、各种各样的文人墨客的笔下,乡情得到最动人心弦的表达。这可能给人一种错觉,仿佛乡情仅仅属于这些多愁善感的文化人!真的,无缘诗书、甚至目不识丁、表情木然的底层草根,也有乡情吗?乡情不是一种细腻、优雅的高等情调吗?我宁可认为:没有比这更荒唐的误解了!乡情属于所有天下人,它弥漫于自茅舍至宫廷的大地。地地道道的贵族楚霸王项羽,落魄于乌江边仰望江东时,心中那不能自已的一腔乡情,与某个返乡路上的游子的乡情,难道会判然有别吗?
我们生活在一块特别看重故乡的土地上,对于故乡的眷恋很不同于闯浪天下、四海为家的西方探险者。我们无从知道,哥伦布、麦哲伦、皮萨罗以及利玛窦等人是否记得自己的故乡,是否也有思乡之情。难道乡情不是中国人所特有、是中国这种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特产吗?你听到哪个西方人说过“叶落归根”?
这又是一种误解,可能是一种更难破除的误解!人类有一些东西方共有的感情,乡情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没有乡情,华盛顿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,为何要那样急匆匆地返回他那日思夜想的弗农山庄?如果没有乡情,几乎已在美国生根的索尔仁尼琴,为何要义无反顾地返回俄罗斯故乡?他仅仅是为了能够埋骨故土吗?
这就应当承认:乡情属于全人类,它源于共同的人性,并不是某种特殊文化的产物;乡情的力量源于普世的情怀,全人类都能认识、理解与体验它,并不需要基于什么特定的文化教养。
对于乡情价值普遍性的认知,就只能到此为止;否则,就走过头了!现在就要开始强调:乡情所展示的力量,在不同时空之下相差悬殊,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大半辈子蛰居伦敦的马克思,与始终眷恋着河南项城的袁世凯,可能有同样的乡情吗?西方人的普遍乡情淡薄与中国人的浓厚乡情,是文人们的轻薄杜撰吗?毋宁说,这种差别恰恰展示了乡情的不同背景。
在根本的意义上,乡情终究是农耕社会的产物;不妨说,中国正是农耕社会的故乡。鉴乎此,就不难理解,中国人具有全世界最执着的乡情。也能理解,乡情终究是一种狭隘、保守、封闭、落伍的传统感情,它不太可能与世长存!
知乎此,你吟诵《床前明月光》时的那种内心激动,能不立减三分吗?
跳出乡缘外
在你呱呱落地的那一刻,乡情就在你的心上种下了。这岂不表明,乡情就是与生俱来的吗?鉴于此,乡情之重再无需多说。但是,你“生于故乡”这件事,究竟有多大意义呢?它有什么必然性吗?不管你是否思考过这件事,都不能不承认:某块地方成为你的故乡,绝对是一个零概率事件,毫无必然性可言!今天的人已不信什么灵魂了。如果姑妄信之,你不妨想象一下,当你出生前灵魂游荡于世界、四处寻觅投胎之地时,该有多大的随机性!你的灵魂落在英国尼斯湖畔,还是落在印度恒河边,岂不都属偶然而又偶然的事吗?
如此说来,某个地方成为阁下的故里,实在毫无神圣性可言,无论你是国王还是草民。对于鲁迅的崇拜者而言,在绍兴某地挂出“鲁迅故居”这块牌子,无疑是一个值得额手称庆的重大事件。但对于1881年(鲁迅的生年)之前的某个预言家来说,1881年出生的中国大文豪降生于何处,则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,没有什么颠簸不破的理由,足以说明鲁迅就不能出生在同样文化发达的苏州某地——倘若那样,鲁迅多半不会再叫鲁迅了!
认识到这一点,对于乡缘——亦即乡里缘分或者乡缘里分——就不会再抱绝对的信仰了。生当一个开放的文明社会,完全没有必要让自己深陷于那妙不可测的乡缘中。
乡缘固然温馨甜美,但跳出乡缘的那种自由自在,不更令人称心如意吗?
只是你会说,乡缘乃人情之常,跳出与否都不是什么天下大事,值得郑重其事地铺叙著文吗?此中岂有深意在?
中国古代有大禹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传说,烟远无据,且不说它。邓小平功业之大,在现代中国几乎无人可匹;他在16岁时离开四川广安赴法留学,此后竟然从未踏足广安!最伟大的现代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,出生并成长于奥地利,中年时任教伦敦经济学院并获英国国籍,此后主要流连于美国学界。同样曾经是奥地利人的爱因斯坦,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都在美国度过。
在特别看重“衣锦还乡”的中国人看来,上面这些人的选择都是不可理解的,他们都乡情淡薄吗?他们竟无意回报乡梓,这是一种缺陷吗?他们都功成名就,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人物,当然不妨遵循不同于常人的行为逻辑。但即使在普通人中,作出类似选择者亦大有人在,许多在大洋彼岸安家的中国学人就是如此。他们选择的理由或许各有不同,但所作选择都促成了各自事业的成功,则是共同的。
这岂不是说,追求事业目标者不妨“跳出乡缘”吗?
如果“跳出乡缘”成了一种普遍的选择,成了一种潮流,成了一种被羡慕的榜样,那么,它就成了一种正常的文明心态,是现代社会开放性的必然结果,不仅不应受到任何指责,而且应成为一种受到鼓励的时尚。说来实在很自然:既然乡缘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的结果,那么有什么理由,要让它成为束缚个人终身的缰绳呢?
世界公民
上面只是说明了,跳出乡缘是可以接受的,它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或许,更值得关注的是,选择跳出乡缘可能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后果。
跳出乡缘之后,会获得多得不可比拟的机会,去选择个人愿意投身的事业;同时也有了不可胜数的机会,获得属意的身份。你将成为工匠还是学者,不再决定于你的故土。即使每个人都持此想法,也不见得都能遂愿。但可以肯定,离乡谋生者将越来越多,其中的成功者亦将越来越多,他们将走得越来越远,更换处所也将越来越频繁、更少顾忌。最终会出现最自由自在的少数人,他们根本不在乎固守一地,而是在这个星球上随意择善而居,完全依据自己的意愿与能力来选择工作与生活地,将传统的故土及祖国概念抛诸九霄云外!
于是,他们成了世界公民。
这看来有点匪夷所思,甚至近于离经叛道,在一个未开放的国家或者未开放的时代尤其如此。仅仅一代人之前,即使是“不安心在家乡工作”的人,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;想离开祖国外出学习或谋生,则更会被斥为叛徒!在那时,无论提出还是想象“世界公民”这种身份,都是大逆不道!但贬斥世界公民的人多半未曾想:最著名的一个世界公民不是别人,正是老祖宗马克思!马克思不仅是事实上的世界公民,而且也公开承认自己的世界公民意愿,还宣称他“没有祖国”!但当他进而宣布全世界的工人都无祖国时,人们就有理由担心:工人们能够认同吗?绝大多数工人毕竟成不了马克思啊!
马克思是世界公民没错。但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,以为自己也有资格当世界公民。你毕竟不是马克思,也多半成不了马克思!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,有资格当世界公民的都是大人物。郎平做世界公民的机会一点不比马克思少:何处不乐意聘请郎平去当排球教练!
我常常想,一个能容纳马克思为世界公民的世界,总不至于太坏!这一点,聪慧睿智如马克思,不可能看不出来。不知道的只是,看出了这一点的马克思,是否还要坚定地摧毁这个世界呢?合理的解释或许是:他认定摧毁了旧世界之后,新建立的世界仍然能保留旧世界的种种好事,尤其保留大学者成为世界公民的充足机会!
或许,这正是天真知识分子——包括马克思本人——的悲剧。
世界公民的出现将引导什么潮流呢?这件事并不简单,没法在此深谈。容易指出的是:世界公民的日益增多,将形成一股具有全球视野、全球关注的力量;随着这股力量的与日俱增,世界将成为愈来愈紧密联系的共同体。目前的世界正在以愈来愈强劲的势头趋向这一前景。你想必知道,这股潮流唤做全球化!
显然,世界公民正是全球化的最激进的主张者与推进者。全球化的推进者与乡缘的距离,已经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了。
宁留乡缘中?
如果你不以为侮,那就让我不客气地说,你成为世界公民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倘若如此,那你就一心一意去做一国之公民、或者一市之市民、甚至一乡之乡民吧。这样你更有可能长期留在乡缘中。其实,这并没有什么不好,仍然可以乐在其中。我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这样活着、传宗接代,直至给你我留下这块乡土。你不认为这已经功德无量吗?如果所有的先民都不恋乡土、居无定所,且不说你今天多半无所适从,是否有“你”存在都成问题!
当然,并不存在“安居乡土”与当“世界公民”二选一的问题,两者之间还有多不胜数的中间选择。值得关注的是,作中间选择者将如何对待乡缘呢?他会有足够的乡情吗?他会偶然或者经常陷入思乡之情吗?对此,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。
古代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中国:大多数文人是陶渊明的仰慕者;所有获取功名之后为官一方的士人,在致仕(即退休)之日,都急急回归乡里,与农夫渔翁为伴,过着世代相承的田园生活,完成他的最后一段乡缘。正是他们留下了无数刻意赞美乡土、乡情的文字,这些构成传统文化中最接地气的一部分。辛亥之后,这样一个中国就一天天远去,今天则近于完全消失。
但是,这个在现实中已经消失的乡土中国,在文学中却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。致力于保存乡土中国的最著名的作家有两个:沈从文与刘绍棠,其主要创作期分别为1949年以前与1949年之后。此处只说沈从文。有人认为,沈从文是莫言之前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,我不知道是否如此;我只能说,如果他获得诺贝尔奖,以其文学成就来说,确实当之无愧。这个当年狂追著名的苏州张家四女之一张兆和的浪漫痴男子,其实一点也不时髦,是一个地道的“乡下人”。他对故乡(湘西凤凰)观察之独到、深入与冷峻,让其作品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中国。与之对照,诺贝尔奖得主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却未必成功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拉美国家哥伦比亚!
此后,即使在文学中,乡土中国也几乎消失了。扫荡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,也迅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——这一点其实与国家的实质性进步关系并不很大。今天,就是沈从文的故乡,其外在形象与生活习俗,也快追上欧美了,那里不再有旧日乡土可寻;那个曾经被沈从文热恋过的乡里,已经消失了,到哪里去找回当年的乡情?今天,湘西的“乡下人”每年都成群结队地奔赴沿海打工地,任何略堪人意的谋生机会,都会使他们一去不复返。他们看重的乡缘能有几何?如果沈从文复活了,他会因此而一洒伤心之泪吗?
乡土很小,而祖国很大,地球则更大。现代化大潮正在迅速铲除阻碍人们自由流动的障碍——这就是今天所有人面对的基本现实。在这种强劲的时代潮流面前,即使是最伟大作家笔下的娓娓乡情,也不太可能打动世人,奈何?